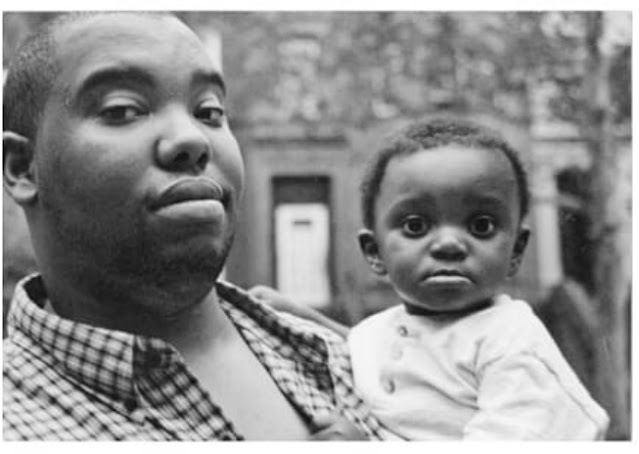2021桃園鍾肇政文學獎文學寫作營(一)百年不孤獨的文學擱淺中,聽村上先生談寫作技藝

48 小時之前,你不認識我不認識你,我們都心甘情願帶上文學的鐐銬,擱淺在桃園婦女館的鍾肇政文學獎文學寫作營中。 帶著鐐銬要如何舞動?當市場和習慣同時產生偏移,導致作者和讀者的雙重傷害時,各位是如何抑不住激動(畸形)的文學愛來到這裡的? 夏至初秋,天天晴空萬里,熱度只在黎明和日暮時稍有減弱。導師高翊峰在開場白中說了一則生活趣事: 「出門前隨意抓了一件西裝外套,到達教室後發現胸前鼓鼓的,一探進去,從口袋中拿出一張名片,沒想到是不久前在活動中與桃園市市長交換來的名片。 記憶如灰燼,散在風中即逝去,卻也是繩索,將奇怪 看似不相關的事黏起來,就像這張名片。 當時他參加活動時不曉得自己會在桃園舉辦的文學營 擔任 導師 ; 當他在進行文學營導師的前置準備時,也早已忘卻那個生活插曲 。 」 不在計畫中的都可稱為意外,故事就是由許多個意外組成的,他用這個小故事說明一件事:意外也可以很美麗。 不是刻意的,才夠深刻。 文學的魅力在於它有時使人沉入往日的夢境,有時又給人冥想後的清明 。意念這玩意兒沒有界線與障礙,它不僅是記憶,不僅是故事,更是一種力量。 文學是什麼? 沒有正確答案 。 但我想它不該是故弄玄虛 ,不該胡說八道,更不該受困於流量的追求與環境的禁錮 。 日漸臃腫的故事文本中,不落俗套的少之又少。寫作者都想與眾不同,但要不是題材太少,故事太老,就是劇情太雷同,人物太單薄。究竟職業作家們是如何寫作的? 高老師再分享一則故事: 「 日本文壇有兩位 家喻戶曉 的 男性 作家,剛好都姓 『村上 』。 一位是村上龍,一位是村上春樹 。 有次,兩位村上先生一同接受訪問,被問到他們是如何寫作的? 村上龍說: 『 我的腦海裡有一幅圖像,我用文字將圖像呈現在紙上 。』 村上春樹說: 『 我先寫出一個字,從那個字延伸出下一個字,再往下寫一個字,一個字一個字組成一句話,一句話一句話串成一個段落,一個段落一個段落連成一篇文章,篇篇相連,字字相印,一本書就這樣完成了 。』」 你喜歡哪種方式?你適合哪種方式?你會不會有跟他們都不同的、屬於自己的寫作方式? 課間休息時我回想著這件事,壓抑乏味的心情忽而產生了幾分期待。